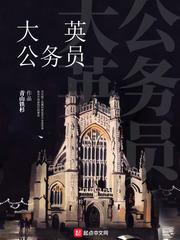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穿成带娃和离妇,盖房囤粮当首富 > 第二百一十章 见世面(第2页)
第二百一十章 见世面(第2页)
更难得的是,在苏玉娘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下,他的思维并不僵化,看待问题往往能跳出纯粹的书本理论,结合实际情况,提出一些朴素却颇有见地的看法。
比如谈到农桑,他能联系到自家种土豆的经验;谈到民生,他会想起铺子里那些普通顾客的抱怨和期盼。
他的回答,虽然有时还带着少年的青涩,但总能条理清晰,不卑不亢,既有书本上的道理,又不乏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,这让周县令越发欣赏。
一次,车队行至一处名为“望月镇”的大驿站歇脚。
这驿站地处交通要道,南来北往的客商、官差极多,显得格外繁忙,也有些混乱。
恰巧一批插着“军需”旗号、押运着不知是粮草还是其他物资的队伍也在此停留。
不知是为了争抢马厩草料,还是因为驿站提供的饭食分配不均,几名负责押运的、穿着号衣的官兵竟在院子里争吵起来,言语粗鲁,情绪激动,甚至拔出了腰间的佩刀,眼看就要动手火并。
驿站的驿丞急得满头大汗,带着几个驿卒上前劝解,却被那些骄横的兵士一把推开,根本弹压不住。院子里其他歇脚的客商也都吓得纷纷躲避,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
周县令和李师爷见状,脸色一沉,正要上前亮明身份进行干预。
就在这时,一直跟在苏老汉身后的苏家仁却突然上前一步,对着那几个剑拔弩张的官兵,朗声说道,声音不大,却异常清晰,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听见:“各位军爷辛苦!小子苏家仁,见过各位军爷!”
他先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,然后才不慌不忙地继续道:“小子斗胆请问,各位军爷身负皇命,押运军需,本该同心协力,共赴国事。如今国难当头,旱情严重,边关或有战事,百姓嗷嗷待哺,朝廷拨下粮草物资,实属不易。诸位皆是为国效力之人,理应体恤朝廷不易,珍惜民脂民膏,又何苦为了些许驿站分配的小事而刀兵相向,内讧不休?”
“军爷们如此争执,非但于事无补,反误了行程,更让旁观众人看了笑话,岂非有损我大乾军威?若因此耽搁了军机大事,或是引发哗变,惊扰了地方,上峰怪罪下来,怕是各位军爷都难辞其咎吧?”
“依小子愚见,驿站自有驿站的规矩,粮草分配也自有章程。军爷们何不暂息雷霆之怒,平心静气,请驿丞大人按规矩公断,或者各退一步,以大局为重,早些用饭歇息,明日也好继续赶路要紧?”
他一番话说得条理分明,既点明了他们的职责和后果,又给足了他们面子,还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。言辞恳切,态度恭敬,却又带着一股凛然的正气。
那几个原本还怒目相向、拔刀欲斗的官兵,被他这番话说得都是一愣,随即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。
他们相互看了看,又看了看周围那些指指点点的客商,再看看这个年纪轻轻却言辞有度的少年郎,心里的火气竟也消了大半。
其中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,最终悻悻地还刀入鞘,对着驿丞粗声道:“罢了!就听这小兄弟的!驿丞,你来说说,这草料到底该怎么分!”
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冲突,竟被苏家仁这几句话给巧妙地化解了。
周县令在不远处看着,眼中露出毫不掩饰的赞许和惊喜。他对身边的李师爷低声道:“景明,你看这苏家小子,不过十四五岁年纪,竟有如此胆识和急智!临危不乱,言辞有度,还能引经据典,以理服人,实在是……是个可造之材啊!
李师爷也捻须缓缓点头,一向严肃的脸上也难得露出一丝赞赏:“宠辱不惊,心怀大局,言行有度,确有几分其母之风骨。此子若好生栽培,将来成就,或不在其母之下。“
车队继续前行,夜宿在一个地图上都未曾标识的、极其破败偏僻的小山村。
因旱情影响,这个小山村几乎十室九空,留下的大多是些老弱病残。
夜晚山风寒冷刺骨,许多人家的屋顶都漏着风,却连取暖的柴火都凑不齐。
苏家仁跟着苏玉娘去给村里送些多余的干粮和药品时,看到一个约莫五六岁、衣衫褴褛得几乎遮不住身体的小女孩,光着脚丫蜷缩在一个破败的土地庙墙角,冻得瑟瑟发抖,嘴唇都发紫了。
当时天色已晚,寒风凛冽。苏家仁看着那小女孩孤零零的样子,沉默了片刻,便将自己身上带着的、准备路上充饥的两个还带着余温的玉米饼,和一小块碎银,大概十几文钱,是他攒下的零花,悄悄地塞到了女孩怀里。看到女孩依旧冻得发抖,他又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身上那件虽然不算厚实、但至少能挡风的细棉布外衣,轻轻披在了女孩身上。
做完这一切,他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摸了摸女孩儿冻得冰凉的小手,便转身快步跟上了前面的母亲。
这一切,恰好被不放心出来查看情况的周县令看在眼里。
他站在暗处,没有出声,只是默默地看着苏家仁那略显单薄却坚定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,才转身离开。
回到临时安排的住处,周县令特意将苏玉娘请来,感慨道:“安康乡君,你教子有方啊!”
苏玉娘有些不明所以。
周县令便将刚才看到的一幕说了出来,语气里满是赞赏:“家仁这孩子,不仅聪慧明理,更难得的是怀有一颗‘民胞物与’的仁善之心!小小年纪,身处困顿,却能推己及人,体恤生民之苦。此等心性,实乃将来国之栋梁的根基!其前途,不可限量啊!”
苏玉娘闻言,心中自是无比骄傲和欣慰,面上却依旧谦虚道:“大人谬赞了。孩子还小,见识浅薄,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之事,还需多多历练,向大人和各位前辈学习才是。”
周县令笑着摆了摆手:“乡君不必过谦。璞玉之质,无需雕琢亦有华光。待回到京城,若有机会,本官倒想看看,能否为他在国子监或哪位大儒门下寻个更好的进学之途。”
这已是存了十分明显的栽培之意了。
苏玉娘心中感激,连忙起身道谢。
就这样,一路行来,苏家仁的沉稳、聪慧、善良和担当,都给周县令等人留下了极其深刻且极佳的印象。
这位原本只是被母亲带来“见世面”的少年,竟在不知不觉中,为自己,也为苏家,赢得了更多宝贵的认可和未来的机遇。
车轮滚滚向前,官道两旁的景致渐渐变得繁华起来,路上的行人车马也日益增多。空气中,似乎都弥漫着一股不同于垚县的、属于京畿重地的独特气息。
苏家仁扒在车窗边,望着远处那在晨曦中若隐若现、连绵起伏的巍峨城郭轮廓,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京城,他们终于到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