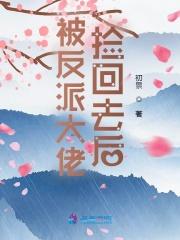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黎民报社 > 过往(第2页)
过往(第2页)
孟允抒记得,许昭是二十四岁时中了探花,而后一年两人成婚,时间对得上。
“初入官场,我想法单纯,性格耿直,空有满腔抱负却不懂得圆滑处事,故而得罪了不少人,却也因此结交了两三个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。”
孟允抒心想,许昭的作风倒是一直都没怎么变。
“绥宁县距京城两千里远,皇上和高层官员都鞭长莫及,当时的知县只手遮天,与通判沆瀣一气搜刮民脂民膏。我与那些好友发现此事,就在暗中搜集证据,打算绕过他们,直接将罪证呈往上级。”
铲除地头蛇绝非易事,孟允抒不由得紧张起来:“结果如何?”
“有人走漏了风声。知县得知此事,寻个由头将我们几人的家眷请到他府中,其中包括我母亲。他假意请客,实际上是想控制住他们,用他们的性命作为要挟,并让他们写信劝诫,让我们就此罢手。”
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中,孟允抒难以想象,如果当事人是她自己,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
“我没有犹豫太久,因为我母亲没有给我留时间。”
许昭的声音变得沙哑,眼中逐渐蒙上一层水雾。
“她知晓内情后,当面大骂知县狗官,说她绝不会被他利用,让他奸计得逞。她高呼一声‘苍生何苦’,当即撞墙而亡,血溅知县府。”
她死得决绝,壮烈,有气节。
一滴眼泪从许昭面庞上骤然坠落,砸在他的手背上,迸出一朵碎裂的水花。
孟允抒被他母亲以死明志的行为深深触动,只是沉默地伸出手指,轻轻拭去许昭手背上的泪痕。
许昭平复心情,继续讲了下去。
“我没了后顾之忧,但其他人并非如此。有些人选择向知县倒戈,有些人同我一样东躲西藏,最后成功让此事上达天听。在这一过程中,我的挚友与我反目成仇,也有几人命丧黄泉。”
孟允抒看向许昭朦胧的泪眼,心情十分沉重。
她和许昭心里都清楚,他所做的事完全正确,可它的代价实在太过惨痛。他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,同时也输得一无所有。
“后来我到京城做官,终于见到众人口中的繁华盛景。但我与亲友的约定却一个都没有实现。”
许昭泣不成声。
“中举那天,我高兴地对我娘说,从此之后她不必再住漏风的破屋,能有一床完整的被褥,不用去市集上捡别人丢掉的烂菜叶。”
“在我小时候,她就常常站在田间地头眺望。我问她在看什么,她说她在想象京城人的生活。我对她承诺,我一定会做上京官,带她去往天子脚下。可她熬了一辈子,最终也没能看一眼京城。”
“对我那些好友来说也一样。起初我们互相打趣,若有一人飞黄腾达,就邀请其余人去皇都游玩。等我到了此处定居后才发现,我已不知该将请柬寄给何人了。”
许昭的话语被啜泣揉成七零八落的字词,声调也抖得厉害。
“从那时起我意识到,政治远比我想得复杂。我不愿再经历这般折磨,也不想看到亲友因我遭殃,索性从一开始就不同他人产生纠葛。”
这句话为许昭此前的矛盾表现做出了解释。他不怕得罪人,却对所有人都保持着置身事外的疏离态度。
孟允抒所从事的也算高危职业,她理解许昭的想法。无牵无挂自然一身轻松,没有软肋就不会被他人威胁,更不会有人因他无辜受害。
但许昭并非铁石心肠,仍对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心向往之。否则他今日也不会讲述这些事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孟允抒握住他的手,温声说道,“我不会直接替公子做出选择,这样是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你。只有你自己想明白了,才能得出想要的答案。”
“但我可以帮你扪心自问。”
她笑了笑,话锋一转。
“请问公子,在你揭发知县罪行之前,你与身旁亲友过得是否开心?”